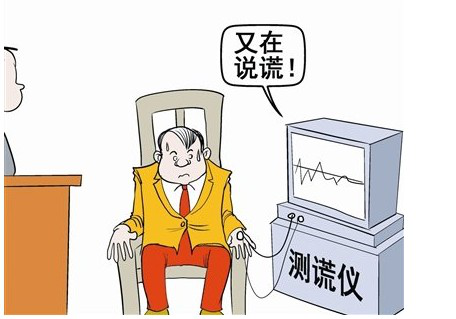
“我愿做中国第一个敢于公开接受测谎的‘贪官’。”浙江省诸暨市人社局原局长金伟法一审被判10年6个月后,提出上诉,12月20日,他手书呼吁信,请求绍兴中院二审时当庭对其进行测谎。
金伟法同时放出狠话:“如当庭测谎发现我在受贿问题(是否收受贿赂款、是否藏匿贿赂款)上有任何说谎的成分,我愿意服从二审法院的任何裁判,并不再申诉。”
澎湃新闻从金案的诉讼材料中获知,一审围绕该案侦查期间的测谎报告是否应当出示,控辩双方争论激烈。最终检方以测谎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为由,不予出示。而金伟法及其辩护人均认为,该测谎报告可能对金伟法有利,应当出示。
国内证据法学专家认为,金伟法案暴露了我国目前刑事司法领域中测谎结论在法律地位上的尴尬,但在司法实践中测谎已被广泛运用,亟待立法予以规范完善。
庭审焦点:测谎报告要不要出示
案发前,金伟法为浙江省诸暨市人力与社会保障局局长。
2015年7月1日,诸暨市检察院向诸暨市法院起诉,指控金伟法在担任诸暨市浣东街道党工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毛某等4人360万元;担任“浣东街道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组长时滥用职权,让两户居民的违章建筑获得了拆迁补偿。
一审判决书显示,2016年3月25日、4月5日,诸暨市法院两次开庭审理金伟法案,金当庭否认有罪供述,律师也为其做无罪辩护。
一审庭审中,由于三名证人无一出庭作证,检察院工作人员在侦查期间给金伟法所做的测谎结论是否应出示,成为庭审中的一个焦点。
据金伟法的自书材料陈述,2015年9月中旬,诸暨检察院的两名工作人员及一名自称来自省检察院的测谎专家对他进行了测谎。测谎结束后,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他:“尽管这不能作为证据,但我们一定会把测谎报告交给审判长巩固心证。”
由于在此后的庭审中,该测谎报告并未公开出示,也未提供给审判长“巩固心证”,引发金伟法和律师的当庭质疑,认为是检方隐匿了有利于金伟法的证据。
据参与一审庭审的多名人士回忆,审判长曾发问公诉人:“2015年9月份金伟法所做的心理测试,有无形成书面报告?”公诉人未直接回应是否形成书面报告,并称心理测试只是作为判断证据的方向,通过心理测试而发现的证据已向法庭提交,根据相关规定,心理测试的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检方最终未出示该测谎报告。
辩护人、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章雨润律师质疑,公诉人甚至当庭宣读了部分测谎结论,说明检方对金伟法的测谎已形成书面报告,不出示的原因很可能是测谎结论对金伟法本人有利。
庭后,辩护律师申请法院依法向浙江省检察院调取该院受诸暨市检察院委托,指派心理测试鉴定人对金伟法进行心理测试形成的《心理测试检验意见书》正、副本以及测前、测后谈话提纲及谈话记录,测试题目、测试记录、测试图表以及其他相关材料,但未获回应。
章雨润认为,检察院侦查案件和提起公诉,应当遵循客观公正原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也有义务收集和举示,“测谎结果有利于指控,即为‘我’所用;有利于被告人,就说它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向法庭出示,这样的逻辑对被告人不公平。”
2016年11月20日,在多次延长审限之后,诸暨市法院一审认定金伟法滥用职权罪不成立、受贿358万元,对其判刑10年6个月。金伟法不服上诉,随后向二审法院绍兴中院提出了调取侦查期间测谎结论的申请。
金伟法在其自书的呼吁信中,还请求绍兴中院二审时对其当庭测谎,“如当庭测谎发现我在受贿问题(是否收受贿赂款、是否藏匿贿赂款)上有任何说谎的成分,我愿意服从二审法院的任何裁判,并不再申诉。”
就金伟法案测谎是否形成了书面报告、检方为何不提交给法庭等问题,12月29日,澎湃新闻联系了该案的公诉人、诸暨市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郦纪城,她表示,该案现已进入二审,希望澎湃新闻采访上级检察院;同时,她需要经院办公室才能接受采访。
澎湃新闻随后与诸暨市检察院办公室联系并发送采访函及采访提纲,截至发稿尚未收到院方反馈。
职务犯罪推广测谎,结论怎么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介绍,CPS多道心理测试,俗称测谎,是一种20世纪20、3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技术,我国对测谎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和研究测谎技术,并首先运用于刑事侦查。
199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批复四川省检察院的请示中,明确规定:CPS多道心理测试(俗称测谎)鉴定结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结论不同,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
在此期间,检察系统内极少使用测谎来配合侦查。2009年,这一情况开始改变,最高检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心理测试技术工作程序规则(试行)》文件,明确全国检察技术部门开展心理测试工作。
此后,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还曾下发《2014年检察技术和信息化工作要点》,明确指出,要重点发展心理测试等业务板块,服务、引导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自此,各地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开始大量使用测谎。
据《合肥晚报》报道,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检察院2013年开始采用测谎仪查办犯罪案件,“并成功侦破了3起自侦职务犯罪案件和10余件非自侦刑事案件,测试准确率达100%。”
《检察日报》报道称,2013年以来,云南省检察机关有9个检察院装备了心理测试技术设备,有8个检察院已运用心理测试技术辅助办案,办理案件100余件次。“心理测试工作在协助自侦部门讯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讯问效率和成果。”
正义网2016年12月2日的一篇关于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的介绍中显示,该检察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已配备侦查测谎仪等各类侦查技术装备,为检察工作的发展提供高端技术保障,“实现职务犯罪的‘云侦查’”。金伟法在其自书材料中亦提及,检方人士来给他测谎时,提及测谎设备是“刚刚花了三十多万元装备的”。
专家:测谎不能做“入罪”证明,但可做“出罪”证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中认为,既然是检察机关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测谎,那么测谎结果就应该告知当事人。不过,根据最高检1999年的批复,检察院在办理案件时,可以使用测谎结果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向法庭出示和质证。
换而言之,金伟法案暴露了目前测谎技术在中国刑事侦查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检察机关开始装备心理测试仪器、大量使用测谎来配合侦查,一方面是测谎结论在法律上地位的缺失——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利的测谎结论,在现行法律下不能用来指控犯罪;对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利的测谎结论,也不能拿来作为被告人“自证清白”的证明。
测谎究竟该如何规范?易延友教授认为,虽不作为证据使用,但测谎应当形成报告,也要提交法庭。对于最高检1999年的批复,“应当理解为只是说测谎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却没有说不能作为辩护的依据”。
“相比一些刑事案件中可以考察凶器、生理材料等等物证,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往往非常单一,很大程度上依赖口供,这也导致嫌疑人和被告人其实很难自证清白。”易延友说,“如果一个受贿案件的嫌疑人能够通过测谎,我们不能说他就一定没有说谎或者没有受贿,但是,这份测谎结论对于当事人和律师的辩护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是一份能佐证其清白的重要旁据。”
作为一审被定罪量刑的“贪官”,金伟法要求二审法院对其进行当庭测谎以自证清白,这一要求是否能得到法院支持,尚未可知。金伟法的辩护律师表示,目前金伟法刚刚上诉,律师还没有就具体问题与二审法院交流。
澎湃新闻查询有关媒体报道,早在2011年6月,山木培训创始人宋山木涉嫌强奸女员工案庭审期间,宋也曾向深圳中院申请由专业测谎机构对其本人及受害人同时进行测谎测试。宋的律师表示,测谎仪检测出来的结果,可以让法官对双方供述的真实性进行判断,“测谎结果未必一定是对宋山木有利的”。但最终,法院没有允许。
而在民事诉讼领域,将测谎结论引入法庭质证已有先例。2009年8月22日上午,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时,对双方测谎的结论被引入法庭质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易延友认为,近年的司法实践中,测谎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存在的问题是,当办案单位使用心理测试之后,不利于被告人的结论顺理成章用于辅助侦查,但有时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却处于“黑箱”之中,不能辅助法庭查明真相,这明显有违法治原则。
《检察日报》亦刊文称,运用测谎结论需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当测试结论肯定了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时,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可以把它作为证实犯罪的依据;二是当测试结论否定了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时,侦查人员不相信测试结论,而将犯罪嫌疑人继续置于有罪的主观推定中。
易延友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尽快进一步明确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如果仅仅按照最高检1999年的批复,测谎结论一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那么各地搞测谎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
易延友认为,规范适用的基本原则应当是,“不能用作指控犯罪的依据,但在侦查机关已经作了测谎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和辩护人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应当提供给辩方,以便其用作‘出罪’的证据。另外,如果控辩双方就测谎证据达成一致,或者将测谎报告用于质疑另一方证言的真实性,也应当允许。”
易延友还指出,一个人被指控犯罪后,自证清白通常都存在较大的困难,测谎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方式;被告人愿意接受公开测谎,也表明被告人可能确实有冤屈。将测谎报告接纳为证据,将其视为专家意见,与在案其他证据一并进行审查,有利于保障辩护权的实现,也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张中教授认为,从发展趋势看,测谎结果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立法也会作出相应调整,确认其证据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