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年之际,一场突发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病毒蔓延之广,感染之快,令全民忧心。疫情当前,无人言退,法律更是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力保障,刑法作为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无疑必须介入如此突发的公共事件中。在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对于违反疫情期间规定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的案例不胜枚举,然而此罪作为一个兜底性罪名在特殊时期被如此频繁适用,是否存在不当的扩大化,值得深思。
对于疫情期间故意造成病毒传播的行为,《刑法》第114条、115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并规定了两类具体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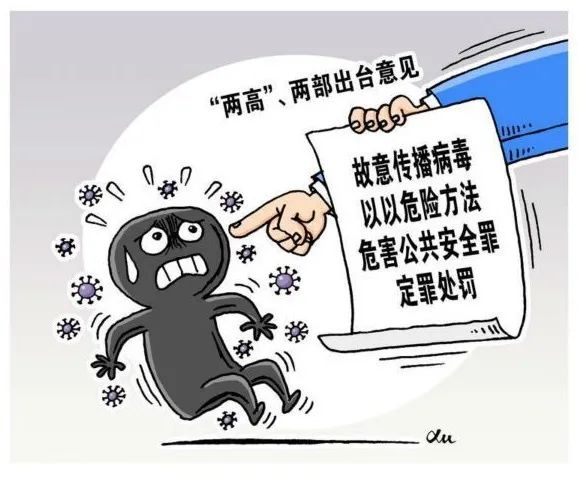
根据《意见》的规定,对于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的行为,要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主体上限于已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新冠肺炎疑似病人;二是主观上具有传播新冠肺炎病原体的故意;三是客观上表现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实施了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其中新冠肺炎疑似病人还要求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后果。从司法实践来看,在疫情期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频繁适用。

案例一:深圳警方通报称,64岁的范某芳隐瞒疫情地行程和发热病情,在乘坐交通工具时未采取防护措施,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其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立案侦查。案例二:山东潍坊警方通报称,1月17-20日去过安徽省蚌埠市的市民张某芳,在返回潍坊途中与他人聚餐,且在返回潍坊后隐瞒旅行史和人员接触史,并于2月2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目前,其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采取相关措施。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行为人确实存在隐瞒行程和病情,并出入公共场所的行为,但此类行为即使在疫情期间,也绝不能“一刀切”的认为是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等方法相当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是应当结合主观故意与客观实际进行综合考量和认定。
1、故意犯罪须明知自身行为的社会意义
刑法评价的是行为人的社会行为而非自然行为。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自身行为的社会意义和可能造成的社会结果。对于疫情期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需要关注的并非隐瞒行为本身是不是犯罪,而是隐瞒自己的病情还到公共场所的行为的社会意义。根据《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所规定的两种情形,行为人应当是在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或者为疑似病例后,仍然拒绝接受隔离,故意前往公共场所,足以导致疾病传播的,才可以认定为故意型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前述两个案例中,行为人均只因隐瞒行程和相应的症状,而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就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采取相关措施。进入公共场所的行为发生在被确诊之前,即使在这期间存在症状也并不能高概率的得出行为人可能罹患新冠肺炎,因此,其主观形态是否应当直接认定为故意值得商榷,直接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疑是对此罪的不当扩大适用。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直接排除行为人间接故意甚至直接故意的可能,但是在实践中应当结合客观实际从严认定,例如:行为人是否拒绝就诊,是否刻意频繁出入公共场所,是否参加了比以往时期更多的公共活动等来进行认定,而不能将行为人隐瞒病情,违反相关防护规定的故意,直接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
2、对“危害公共安全”应从严认定
对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危害了公共安全或者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应当从严认定。由于疫情时期的特殊性,对于公共安全的认定不应单纯通过场所的性质来进行认定,可以结合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数等进行综合认定。首先,对于确诊或疑似患者在公共场所如超市、公共交通工具活动的,可以认定为危害了公共安全,若是在相对空旷、人员很少的场所,不会带来较大范围扩散的情况下,可以酌情不认定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其次,应当关注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例如:即使是在密闭无人的电梯内,向电梯按钮吐口水或者污染一次性用具,也应当认定为危害了公共安全,而若是做好了充足的防护措施在一定场合短暂停留,尽量避免与他人接触,则不应认定为危害了公共安全。

以前述案例二中的张某芳的行为为例,她在返程途中与他人聚餐,是否可以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若张某芳只是在相对封闭的场所进行小规模的聚餐,则不宜认定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对此,应当以聚餐的场所、聚餐规模、人数等进行综合认定。反之,以江某某案件为例:1月21日,江某某驾车到湖北省武汉市一商场购买摄影器材。1月26日,江某某出现咳嗽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症状并前往卫生院就诊,返回家中后,江某某连续多次与不特定人员在多个场所聚餐、参与赌博、利用车辆载客。江某某明知自己存在感染的高度可能性且已经就诊,仍然多次与不特定人员在多个场合进行活动,存在极大的使病毒扩散的可能性,应当认定为危害了公共安全。

3、妥善适用其它罪名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刑法中的一项兜底性罪名,是一项最高可达死刑的重罪,虽然在特殊时期重罪确实存在较好的震慑效应,但是罪刑法定仍然是刑法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更应当妥善适用其它罪名,不仅要做好罪与非罪的考量,也要重视此罪与彼罪的划分。

若行为人只是违反防疫规定,瞒报谎报行程但并未频繁出入公众场所的,或者不遵守相关规定而导致疫情管理难度大大增加的,可视情形依据《刑法》第330条规定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于主观上对危害后果的形成为过失的,可以酌情认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无罪;对于行为人在公共场所向他人吐口水,撕扯他人口罩的行为,若确实不存在传播病毒的故意并且没有造成实害的感染后果的,可以视情形依据《刑法》第293条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可以依照刑法277条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刑法作为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疫情防控是一场全民战争,刑法的介入必须具备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对于疫情引发的种种社会事件,应当坚持民事与行政先行的原则,将刑法作为最后的手段。在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兜底性罪名的扩大化,也要避免刑事手段的扩大化,既要做好此罪与彼罪的划分,更要做好罪与非罪的考量。
作者|安针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