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爆发新冠肺炎以来,因此次“肺炎病毒”来势汹汹,具有极高的“传染率”以及“死亡率”,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提出要“举国之力,控制疫情”,普通公民更是谈“肺炎”色变。在此情况下,全国上下基本形成了一种“无论黑猫白猫,能控制住疫情的就是好猫”的情形。于是任何有利于进一步控制疫情蔓延的行为都得以大行其道,任何有碍疫情防控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个人利益在疫情防治这一大环境下显得微不足道。但笔者认为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即使是在特殊时期也不能一味地高喊着“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是应该平衡好这二者之间的冲突。
一、公民的隐私权与疫情信息公开

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在疫情期间政府需要定期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但由于初期政府防治措施的不力,导致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许多公民对于政府公布的信息大都处于不信任的状态。再加上本次“肺炎病毒”有较长的潜伏期,在感染者不明的情况下,武汉返乡人员就成为了普通民众的恐惧对象。因此在疫情爆发初期,为了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大量武汉返乡人员个人信息通过网络途径被大范围的泄露。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有34%的人员表示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而这些被泄露的个人信息即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还包括身份证号、返乡时间、乘车信息等较为私密的个人信息。
虽说这些信息的公开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他公民提高警惕,不与返乡人员亲密接触,同时也能迫使武汉返乡人员自觉的居家隔离,减少外出,减少二次传播。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些被公开的信息中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与疫情防治有关。例如,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就与疫情防治无关。而这些信息的泄露十分有可能导致歧视,甚至是人身攻击等现象。且如今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不再仅限于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还在于个人信息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价值。此外,信息地泄露还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而实施非法活动。故而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平衡好公民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关系,坚持比例原则,在进行信息公开时应做好信息分离工作,仅公开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信息。同时还应当加强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严禁个人非法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
二、保护人权与疫情社会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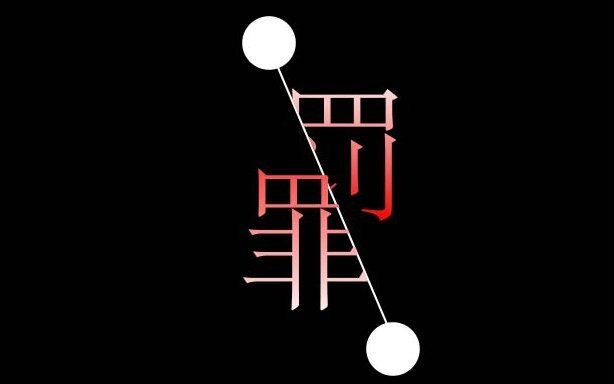
本次疫情爆发后,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根据该《意见》的规定要做到“坚决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用足用好法律规定,依法及时、从严”。而在所有的法律中,刑法无疑是最能做到快速、严厉地打击哄抬物价、不配合疫情防治工作等有碍疫情防控行为的手段了。但是就目前我国情况来看,此次疫情防治期间的刑法治理,却存在过于偏重疫情防控,而罔顾人权与刑法谦抑性之嫌。
例如,2020年2月1日,隆尧县固城镇乡观村干部刘某按照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和镇政府要求,在村中大街劝返聚集的村民,赵某因不满村委会粉刷其家外墙一事与刘某发生口角。次日8时许,赵某持尖刀至村委会办公室,要求村委会恢复其家中外墙原貌,且扬言要自杀,并不许他人接近。村干部劝说无效后报警,民警到场后进行劝阻,赵某情绪激动,多次用尖刀抵住颈部以自杀威胁民警不得靠近。直至13时许,赵振轻放下尖刀,欲点燃随身携带的烟花弹“震天雷”,被现场处置民警制服。最后法院以赵某在村委会滋事约5小时,致使镇村干部不能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为由,判处赵某有期徒刑6个月。但笔者认为,本案中赵某之所以到村委会办公室闹事的原因在于,不满村委会对于其家外墙的不正当粉刷行为,希望村委会能将其家外墙复原,而这非不正当诉求。再者,赵某虽持刀“恐吓”,但持刀恐吓的方式却非是伤人,而是自杀。所谓恐吓一般是指“以恶害相威胁”,而自杀行为并不属于所谓“恶害”,也很难认为认为赵某的自杀威胁能使刘某等人产生恐惧心理,故而笔者认为赵某的行为行为不属于恐吓行为,故而也够不成寻衅滋事罪。
在现今这个特殊的环境之下,用刑法来对一些违反疫情防治秩序的行为进行惩罚确实能起到很好的威慑效果,同时也回应了现阶段民众对于严惩违反疫情防治措施行为的呼声,有利于安抚民众因疫情以及各种疫情防控措施而起的各种不满情绪。但基于这种目的进行的刑法判决却是将刑法视为了社会治理的工具,同时也将人视为了社会治理的工具,违背“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这一理念,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人本思想。疫情期间,司法机关应该保持理性,警惕刑法工具主义,在判案时应坚持刑法条文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才是小前提,将目光来回穿梭在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之间。而非将案件事实作为大前提,二将法律条文作为小前提,随意找个罪名就案结事了。在看重刑法的社会防治功能时也不能置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于不顾。
三、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与疫情防控秩序
3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贾柏岩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法庭里,面对屏幕,审理了一起盗窃案件。而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被告人家属等8人则在8地共同经历了这场在线庭审。受疫情的影响,全国范围的停工,直到前段时间才开始陆续的复工,同时各地交通运输也受到了不同范围的限制,各地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司法秩序的正常运行,许多法院都采取了视听传输技术方式来进行“云庭审”。但由于我国目前线上庭审技术的不成熟性以及此次疫情的突发性,导致全国各地线上庭审模式五花八门。仅以“云庭审APP”为例,诸如网络卡顿、辩护人掉线、被告人找不到庭审入口等事件基本上是家常便饭。但这些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事情却极有可能会影响到诉讼程序参与者的积极性、认真度与参与度,最终导致诉讼当事人的正当的程序权利得不到保障。如在上文提到的盗窃案中,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各处一地,极可能导致控辩双方辩论不充分,使得庭审流于形式。
疫情期间,采用视听传输技术方式开庭,使得庭审可以突破物理上的空间限制,可以很好的缓和“控制疫情”与“维护法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但是若在庭审时仅追求庭审结果,而不顾庭审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则最终侵害的将不止是当事人的权利,而将是司法的神圣性。
四、结语
作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应该时刻谨记“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疫情防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故而不能本末倒置,将控制疫情作为目的,而将人作为手段。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间应坚持比例原则,平衡好公民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