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兴起后,信息产生与传播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每个人都拥有了在公共空间发言的能力。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社会经历了一段短暂停摆的时期,公众较之以往有了更多接触网络信息的时间。因而,个体通过网络传递的信息都在疫情防控期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部分个体传递虚假信息的行为让战疫工作不仅停留于医疗和防控一线,也衍生到了信息确证一线。虚假信息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轻则造成社会公众的心理恐慌,重则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一、“双层社会”的形成
——虚假信息犯罪高发的现实背景
时至今日,网络的普遍化应用和深度化发展以使网络成为了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空间。人们往返与现实与网络之间,且现实生活的顺利进行已无法离开网络技术,跨越现实和网络之间的“双层社会”已经形成。然而,亦如美国学者斯皮内洛所言:“网络会开辟创造与自由的新天地,还会成为罪恶与堕落泛滥的虚拟欢场。”如2020年3月21日,网络上流传一篇名为《我最难忘的一天》的文章,该文主要谈及武汉存在大量瞒报新增病例的情况,让人们怀疑疫情防控是否真的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3月22日凌晨1时43分,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涉疫大数据与流行病学调查组通报:《我最难忘的一天》披露武汉有新增确诊病例的情况不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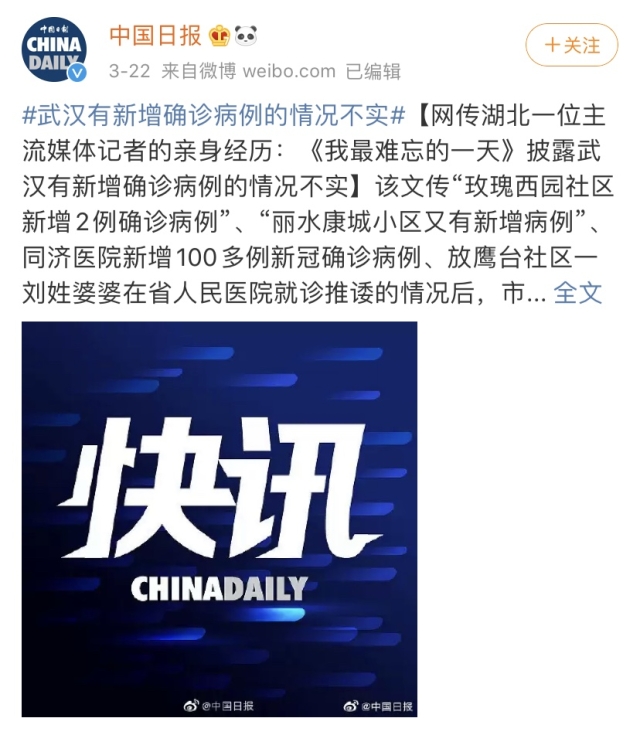
在“双层社会”背景下,虚假信息能够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由于疫情爆发初期,我国地方政府一定程度地隐瞒相关信息导致公信力的缺失,社会公众怀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通过社交网络传播了虚假消息,社会舆论不断发酵、膨胀,最终引起社会恐慌。
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界限
为应对疫情期间社会中出现的虚假信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规定,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
准确理解该罪的构成要件直接决定何种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将面临刑事处罚。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主要应从以下几点加以把握:
首先,要准确定义何谓“编造”、“故意传播”。“编造”是指凭空捏造,其实质内涵在于无中生有。“编造”行为实质是在于创造一种客观不存在的虚假事物,既包括行为人无中生有的捏造、胡乱编造,也包括对一些信息进行“添油加醋”式加工、修改的行为。“传播”是指通过电话、语言、文字以及信息网络等方式散布虚假恐怖信息,使其他个人或者组织知晓该信息。
其次,正确判断“编造”与“故意传播”之间的关系。从刑法规定来看,此两个罪名的行为方式包括编造和故意传播。就编造行为而言,只是单纯地编造而未对虚假信息进行传播的,不应当认定为犯罪。只有在编造虚假信息的基础上,对之加以向不特定公众传播,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就意味着即使是个人记录信息的行为也可能构成犯罪,显然是难以被人接受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若明知自己编造的虚假信息被人传播,而不加以阻止的,应当认为其在主观上具有间接故意,构成相关犯罪。关于“故意传播”,是指行为人在传播之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信息是他人编造的信息而进行传播。即故意传播者并非虚假信息的编造者,其传播的是让人编造的虚假信息。
再次,网络传播行为的准确认定。在网络空间中,对于“自编自传”、放任所编造的虚假信息传播的行为认定难度并不大。但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虚假信息传播者的认定存在一定困难。虚假信息的网络传播过程中还存在转发者,而并非所有转发者都能被认定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来源于虚假信息传播与真实信息披露之间的时间差。而在部分转发者在明知是虚假信息的情况下,企图利用时间差传播虚假信息,从而达到扰乱社会秩序目的。对于此类转发者应当认为其行为属于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另一部分转发者出于新奇或求证信息真实性等原因转发虚假信息的,其并不具有主观恶意,其行为不属于刑法规制范围。
最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结果要件,但立法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公布了《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作出了明确解释。据此,应当认为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罪设定更高法定刑的情况下,本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断标准不应低于《解释》中的规定。
对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一类整体的评价基准的具体适用问题,刘艳红教授认为不但能从客观上予以限制,而且在主观方面,也有限缩的余地:整体的评价要素属于故意的认识和意志的内容,只有当行为人认识到其有害言论之发表会发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等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且无任何正当目的时,方有以言论型犯罪定罪处罚的可能。
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相关罪名的辨析
根据《意见》,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罚。但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一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与前者存在密切联系。
在《刑法修正案 (九)》增加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之后,对本罪“虚假信息”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恐怖信息”的区分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刑法立法规定的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性威胁等恐怖信息自身便具有能够引起公众恐慌的性质,因而对此类恐怖信息的判断并不困难。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公布了《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6条规定,“虚假恐怖信息”包括了虚假的“重大”灾情、疫情信息,对此类信息能否被认定为“恐怖信息”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两者主要不同的是虚假信息的内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将虚假的疫情信息纳入其中。而在解释中, 《解释》以 “重大”一词修饰作为恐怖信息的 “疫情”。由此可见,二者的区别产生于后者添加了“重大”而使得行为危害性的程度有所不同。“虚假恐怖信息”的本质在于信息已经发布,就足以使大多数人惊慌害怕。《解释》以 “重大”一词修饰作为恐怖信息的 “疫情”,“重大”的认定应结合具体的虚假灾情、疫情的传播是否引起或可能引起公众的恐慌、不安或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
四、小结
自疫情发生以来,社会经历了多次舆论浪潮的冲击。当动用刑法对虚假信息进行制裁时,必须慎之又慎,准确区分行为性质是否具有法益侵害性。无论是公民并无主观恶意的转发虚假信息,还是仅对相关事务发表自身看法都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无数的案例已经证明单纯地依靠惩罚无法抑制虚假信息的产生与传播。打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除了要依靠刑法手段,更重要的是官方及时披露真实的信息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只有实现真正的信息对称,虚假信息才难有破坏社会秩序的余地。
作者|王野

